青春梦一场珍惜相聚的时光什么歌(青春梦想演讲稿)
导语:青春梦(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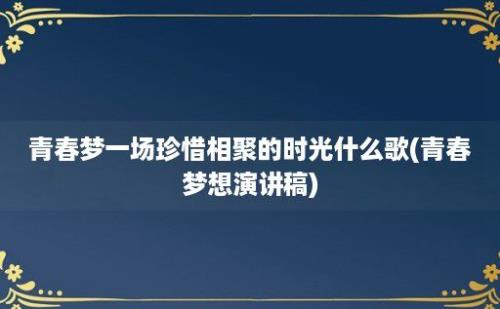
公元1985年,中国腹地江汉平原长湖镇。
张连民走在被一夜春雨洗刷得干干净净的青石板的长湖镇街上,从一边屋脊上方射过来的晨光,叫他那明亮的大眼睛眯成一条线,眉头也随之皱起来,本来恬静的面容出现了疑惑不安的神情。
连民前面四五步走着一位秃顶,秃顶周围花白头发也不多的老头,时不时扭头望他一眼,眼神充满了沮丧与无奈。 这位老头就是连民的父亲张友新,今天带着儿子去自己干了三十多年的日渐衰败的长湖橡胶厂上班。
虽然儿子对被安排到这个厂工作并无多少怨言,但他为儿子能进好一点的单位不知跑了多少路,求了多少人,当然,靠他那一文不值的老面和一瓶罐头一瓶酒每次都是徒劳。为此,他不知偷偷流过多少老泪,他真不想让儿子又来尝自己吃的那些苦头。而儿子认为到哪里干都是干活拿工资,不必那样挑肥拣瘦。
连民脚下平整的青石板街面变成凹凸不平的煤碴道路后,一拐弯,顺着一条二三十米长的小路望去便能见长湖橡胶厂的那两扇歪歪扭扭的缺了几块板子的木板门,走到门口,眼前是几栋灰色的较大瓦房围成的长方形院子,还有院子里的大杨树。
父子俩走进空无一人的院子,办公室门还锁着,旁边屋子里有零星的锤锤打打的声音,说明有人开始干活了。他们俩默默地站了一会儿,厂长还没来,父亲对连民说:“等赵厂长来了,你说是来工作的,他会安排活你干,我干活去了。”连民认识赵瑞,便点点头让父亲走了。
连民仔细打量起四周,父亲呆了几十年的厂,他当然来的次数不少,但从未像今天看得这样入神。大门朝西开,大门的两边各一段长满青苔的围墙,其余三面各有一幢一般大的壁面脱落殆尽的瓦房。南面的是职工宿舍,北面的那幢左边分隔出来的两小间分别是领导办公室和财务室,右边的一大间是搞生产的粘贴间;东面的那幢,也分隔成三间,大概是均分从左到右依次是仓库、炼胶间和硫化间,这些名称都用隶书写在每间门的上墙上,字迹已褪色得难认了。
院子四周,也就是三幢瓦房和两段围墙的前面,等距离矗立着几十棵高大的杨树,树身高出瓦房半个身子,枝叶繁茂,带着露的嫩叶在明媚的阳光下显得格外清新苍翠。一人难以抱尽的躯干上布满着弯弯曲曲的深深的树皮纹,这同陈旧瓦房上褪了色的隶书一样,足以把人们的思绪带到久远的年月。
一阵烟香冲淡了橡胶厂固有的橡胶味,这时连民身后有人问:“你来干什么的?”连民扭头见是厂长赵瑞,忙答道:“赵厂长,我是来工作的。”“哦,你就是张师傅的小家伙吧?好,随我来。”赵瑞边走边说,“安排你来我们厂工作,镇劳动服务站早把通知发出去了,怎么今天才来?”连民不知说什么好,一时没吱声,赵瑞便笑道:“肯定是有情绪,是吧?”连民无可奈何地一笑.脸涨红了。因为此时他想到父亲求人无功而返后沮丧与无奈的神情。
说话间,连民少不了打量这位认识但不熟的赵瑞厂长:高个头,大肚子,满脸胖得油光油光,留着短短的头发,使整个脑袋显得圆圆的。连民还想在赵瑞这张奇特但不很难看的脸上找出一点睿智的“官气”——领导干部的那种应有的气质,但只看到他那游移的小眼睛里有一种迷离的神色。赵瑞肥胖得两臂向外撇开了,大摇大摆地走路。
连民跟着他,走到宿舍的右端,只见宿舍与东面那幢房子之间的缝隙有一道很窄的巷,这是刚才连民打量整个院子,所不曾看到的。除站立点正对这道小巷,无论站在哪里都是发现不了的。这道小巷犹如暗道。过了这道小巷尽头的门,走下二三十级石台阶,便到了长湖河宽阔而景色宜人的河滩。
这当儿,连民想到武陵人过窄窄的山口入桃花源的情形。橡胶厂的一道生产工序在这里进行。这时,场上扯着一匹长长的帆布,帆布两端固定,中间由七八个等距离排列的像赛栏似的铁架子撑着,三位妇女正用刷子给帆布刷油漆状的黑橡胶。刷胶后的帆布是去做三角带。干活的三位,见厂长和连民下来,便停下手中的活,目光都落到了连民的身上,连民微窘地说道:“各位好!”赵瑞对最高的那位说:“素芝姐,几天前走了一个,今天给你一得力干将。”赵瑞一面说一面拍连民宽大的肩膀。“这好!这好!”素芝见连民生得壮实眉宇间透着一股灵气,露出欢欣而亲切的笑容。
赵瑞对连民说了声“好好干”嘴里喷着烟雾摇摇晃晃地上去了。连民搓着双手正要问怎么干,素芝轻声说:“你是张师傅的儿子吧?”连民点点头,素芝心里涌出一股惋惜和怜悯之情,关切地说:“怎么安排你干这种活,又脏又累,工分又难挣。”素芝见连民露出了惊异的神情,便强笑道:“反正在这个鬼厂里干什么活都差不多,除非你当管理人员,坐办公室!你既然来了就干吧,好,我们来认识一下。”素芝又指指比自己年纪大的那一位;“她姓刘,可能跟你父亲的年龄差不多,就叫她刘妈吧。”刘妈比素芝矮些,却要胖点,丰满略带褐色的脸膛,端正的五官能表明她年轻时一定是一位漂亮姑娘。
素芝又指指年轻的那一位:“她叫玉秀,一定比你大,那就是玉秀姐了。”玉秀是位十分漂亮的少妇,身段苗条而匀称,秀发披肩,白净的面容略长,却和她笔直纤巧的鼻子和浓眉杏眼浑然一体,十分和谐,一笑薄而有力感的嘴唇往上一收露出洁白整密的牙齿,此时格外美丽。
素芝双手一合,接着说:“我叫素芝,我女儿霞霞不比你小,你就称我素芝姨吧。”素芝比刘妈要年轻得多,却比刘妈要黝黑,皱纹要多,白发也不见得少,一见就知道她吃苦要多,不过也能断定她干活的力气即使是年轻妇女也没法与她比,因为她的四肢像男搬运工那样粗壮。看看她那端庄的面孔,慈眉善目,富有热情,连民想:素芝姨一定是位受人尊敬.惹人喜欢的女人。
素芝介绍完,从胶桶里拿出一把刷子递给连民:“干活吧,没什么技术,就往上刷,要尽量刷均匀点。”“他还没说出自己的名字呢?”玉秀婉尔一笑。“我也忘了,真是死脑筋。”素芝捶头,也笑了。连民无意地挠了一下后脑勺,腼腆地说:“我叫连民,请各位多多关照!”玉秀又笑了:“还真像那么回事——多多关照,关照你多流汗!”“其实,我以前知道你的名字,只是一时记不起来。”刘妈望着手上刷动的刷子说。素芝和玉秀已动手,连民学着他们的样子刷起来。
至此,连民已成为长湖橡胶厂实实在在的一员。刷胶场这地方很幽静,一面是波光磷磷的长湖河水,只是偶尔一轮装满黄砂的机动船隆隆而过,船尖犁起层层波浪,在岸边发出啪啪的声响;东西两边是高高的红砖围墙,因为不是汛期水位很低,围墙的下端没触到河水,围墙外茂密的大小杂树青枝绿叶,各色小鸟在交错盘曲的树枝上啾啾喳喳地乱蹿,动作十分轻捷。围墙内除了常走的地方没草外,其它地方青草长得十分茂盛,离远点看,像给整个刷胶场铺了一层绿色的“地毯”,中间被揭去了长方形的一块。草丛中零星的野花给整个绿色点缀了几点红黄。早春沁人心脾的气息被汽油橡胶给搅浑了,这里的空气难以入鼻,不过时间一长就觉得不那么难受。
下午,连民生怕迟到,丢下碗筷就出了家门。他来至橡胶厂跑到侧门口向下一瞧,刷胶场上空无一人,他返身走了几步,站在宿舍前的一棵杨树旁。忽然有人喊:“连民,这么早,快来我们家坐坐。”是素芝临窗在叫他,他高兴地应了一声,便推门进去。素芝正和女儿霞霞吃饭,连民进来,她连忙把碗筷往桌上一放,起身说:“快坐,吃饭”霞霞迅速从床下拿出一条小板凳向连民递去。“谢谢,你们吃,我刚吃过了。”连民接过板凳说。
他屈腿坐下,两只手来回摸着大腿,不知往哪儿放,显得很拘束,眼睛自然是不便看她们母女俩,怕影响她们吃饭的兴致,打量起整个房间来。
宽与长分别约为三、四米,也就说房间的面积只有十多平方米。窗下一张书桌,书桌左边一张镂花的老式双人床,右边是一架大衣柜,正用着的饭桌在柜与床之间。这些家具都是素芝那时的嫁妆,已用二十多年了,上面暗红色的油漆脱落了一半,衣柜门上写着“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诗句的字迹褪得模糊了。一些日用器具都是旧的毫无色泽,大概只有书桌右上角的那台黑白电视机是新买的。
素芝瞥了一眼连民,笑说:“这房子比螺丝壳大不了多少吧?过几年,等我盖了新房你来我家。就不会像今天坐下腿都不能伸”。“我们家也一样,还不知要过多少年才能自己盖房。”连民说着,脸上泛起惭色。
连民家住的是公租房,是解放初期盖的居民瓦房,早已破旧,只是有几间住着比这宽敞些。“只要好好干,会有这一天的。”素芝应和道。很快,连民有些坐不住了,便顺手在桌上拿一本书翻看起来……坐了好一会儿,连民和素芝一起从屋里出来,通过侧门下河滩,台阶快下完,他忽然感到头顶一阵发热,便记起把草帽丢在素芝家里了。
饭后的霞霞伏案看书,听到一阵急促渐近的脚步声后,随着一句“帽子给忘了”的男音,没闩的门被推开了。霞霞抬起头,见是连民,正想和他说话,但他从壁上拿起挂着的帽子转身跨出门,没看霞霞一眼。霞霞不由自主地扭头瞧窗外小跑的连民,直到他那矫健的身影离开视线所及的范围。她的目光回到书本上,好一会儿书上的铅字像许多无意的黑点……
作者注:长湖橡胶厂采用的工资制度是:记件工资与计时工资相结合。一般的生产讲定额计工分,生产以外的事属杂事讲时间记工分,还有一点要说的是,工龄长的工价高,工龄短的工价低,但达到一个工的定额或时间是一样的。这有些不公平,但也没人反对。那些管理者是固定工资。
本文内容由小德整理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