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离婚经济帮助制度,为何会“效能低下”?

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日趋提升,我国正处于转型升级阶段,婚姻及家庭关系发生了从质变到量变的转变。
量变的地方在于,家庭的总规模越来越小,逐步迈向核心化;质变的地方在于,婚姻的稳定性出现了不足。
例如,从1970年开始至今,随着中国已婚妇女劳动力市场参与率的显著提高,现代女性不仅充当了职业发展的角色,也充当了家庭照顾的角色,面临着双重负担和压力。
相比来说,长期以来,已婚男性的社会角色,却尚未出现本质上的改变。
在此背景下,我国的离婚率不断增高。
如此一来,人们越来越关注夫妻双方在离婚时的个人权益问题,尤其是经济地位处于弱势的一方,其个人权益往往在离婚时受到侵害。

因此,这种利益诉求反映到婚姻法律制度上,就逐渐诞生了特色化的离婚救济制度。
在离婚救济制度体系中,最具特色的当属离婚经济帮助制度,但此制度在司法适用上,表现出了效能低下的问题,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呢?
经济观念的影响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发布,这是苏区第一部婚姻立法,该法在第19条明确指出,离异之后,假如配偶彼此都不想从当前房屋搬出去,那么男方必须把房子的相应区域出租给女方,使得女方的居住所需得到满足。
第20条规定,离异之后,假如女方并未二次婚配,男方必须借助代种田地来维持女方生计,直至女方完成二次婚配。

经过之后的发展,1934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以及1943年的晋察冀边区的婚姻立法,创立了离婚帮助制度。
1950年《婚姻法》第25条规定:“离婚后,一方如未再行结婚而生活困难,他方应帮助维持其生活。”
1980年《婚姻法》进行了改动,将“离婚时”不困难,但是“离婚后”会面临困境的状况被排除在外,明确“给予适当的经济帮助”具体标准。
2001年的《婚姻法》42条和《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27条明确了生活困难应该与绝对标准相适应,同时沿用了“离婚时”这个时间点,指出离婚后出现的困难,不包括在上述救济范畴内,帮助手段是住房亦或其他个人财产,同时指出双方相互协商实现的帮助约定能够被法院确定,协商无效以后才是由法院处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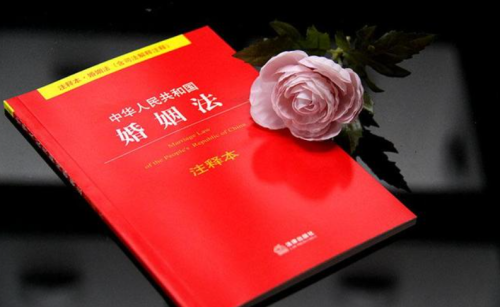
这一阶段婚姻法就离婚经济帮助的可用范围展开了限缩解释,仅仅丰富了经济帮扶的手段,对生活困难的评定使用了绝对论,即不能维持当地最生活水平或没有住房。
离婚时,经济帮助手段是住房的,可认定为房屋的所有权亦或是居住权。
上述制度确定了能够以住房方式提供帮助的法则,但总的来说,与前一阶段相比较,此时婚姻法对离婚经济帮助的适用进行了限缩调整,这主要是受到社会经济进步的影响,我国普遍接受并认可男女平等观念,女性经济地位明显提高,离婚被定义成婚姻双方自由选择的权利,并非只针对单方的重担,这一时期的离婚经济帮助体制表明了婚姻立法的自由趋势。
综合梳理可以看出,在我国离婚经济帮助制度完善的进程里,历经很多段由广泛适用到严格适用的起伏转变,主要是因为过去女性社会地位不高,离婚后很容易变成受害者,要借助提高男方“离婚成本”的手段来对男方的离婚举止执行制约。

但是现阶段,男女平等社会地位平等,女性在社会、家庭中所具有的权利和丈夫是一样的,都有可能获得事业方面的发展和成功,离婚也是以双方平等、自愿为前提。
所以,离婚过程中更加关注男女双方的平等地位,而不是把离婚当成男方或者女方的负担。
由此,影响了离婚经济帮助的适用。
道德观念的影响
道德可以理解为以人们的伦理情感和主观偏向为基础,对事物做出相应认知与正确与否的价值评判。
就人们的主观偏向而言,帮助可以理解为一种慈善行为,虽然我们的道德义务中包括慈善,但慈善是能够以我们个人意愿为前提所选择的义务,可以理解为,我们能够自己挑选履行慈善行为的对象及时间,但是尚未出现一个要求我们一定这样做的权利者。

相较于其他救助行为而言,经济帮助的强制程度更为显著,这一高度强制行为的帮助与人们对救助的一般理解相违背。
就伦理情感而言,帮助应该尽可能以一定情感为基础,最起码是帮助的对象没有伤害过个人的情感。
但是经济帮助体系,反而是把离婚当成请求经济帮助的原因之一。
人尽皆知,中国对是否离婚使用的是破裂主义指标,也就是说,一旦确定情感破裂,夫妻二人就能够离婚。
一般离婚时,男女双方都认为个人的情感遭受了一定程度的伤害。

倘若这个时候生活困顿的一方,请求另一方提供相应的经济帮助,就个人内心的道德评判而言,是无法坦然的,所以不少卷入生活困顿的离婚双方都否认要为另一方带来相应的经济帮助。
显然,内心会直接对伦理情感作出价值评判,被请求方也拒绝为另一方带来经济帮助。
所以,经济帮助体系与人们伦理情感所出现的价值评判及意识和主观偏好不相符合,进而出现经济帮助体系适用率不高的情况。
诉讼观念的影响
贵和是我国传统伦理的关键精神。
和不仅是说和谐、协调,更多是说恰到好处、适中。
儒家指出,婚姻家庭关系和谐的关键就是,每个人要正视个人的地位等级,不要僭越自己的地位等级,同时应该全力履行个人的职责。

基于上述对和谐意识的向往,出现了古代“耻讼”、“无讼”等法律思想。
需要注意的是,就家庭关系而言,古代的百姓更加倾向于大家庭,但是鉴于家庭规模的持续增加,家庭成员间的血缘关系出现淡化现象,家法族规就变成了协调人际关系的关键载体。
因此,只要家族成员之间出现冲突和纠纷,特别是与伦理纲常相关的冲突时,多数还是以家法族规为依据进行处理,而不是国家法律作为解决手段。
近代时期,由于民众权利意识的提高,诉讼观念出现较大程度的改变。
家法族规的地位逐渐被国家法律替代,而且变成处理婚姻双方之间冲突的关键途径。

但是,观念的改变存在一定的连续性,至今未有断裂式进展,所以在观念演变历程里,一般会与很多“传统观念”相伴而生,不少诉讼观念历经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对当前社会的诉讼心理作用仍旧存在。
就现阶段社会而言,只要与婚姻家庭冲突相联系,人们基本上会直接选择“私下解决”。
特别是与经济帮助体系相类似的救济体系,不少人内心依然有顾虑但是不想借助诉讼方式处理。
换句话说,就离婚问题而言,还是有不少人是相对避忌的。
一般情况下,他们认为离婚是“家丑”,更应该“私了”,即使离婚里存在难题也不能够“外扬”,就是说不能借助诉讼手段处理。

基于这一观念的作用,不少能够请求经济帮助的离婚当事人都尚未作出请求,反而接受贫困的状况。
性别观念的影响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宪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都明确规定,男女地位平等是一项基本原则,所以在法律形式上出现了男女两性的平等。
但是即使法律规定形式方面是平等的,但是因为上述法律模式或尚未全面思量到社会地位的法律适用对象之间具有相应的差距,无视或者反对女性的独有经历及不同境遇,使用一刀切的立法方式把相同的权利,配备给了不平等的男性和女性。
所以就适用过程而言,表面中立、公正的法律规定难以获得正义的结局,可能还会扩大两性地位方面的现实差异。

从客观角度出发,我国改革开放后,不少女性在经济、参政议政、保健、教育等更多领域都得到了良好的发展。
但迄今为止,这还是不够的,和男性比较,现阶段我国总体情况而言,妇女地位相对较低。
基于经济帮助体系而言,该体系在执行程序中的不平等直接导致女性财产权益的弱化。
弱化女性财产权益,不仅在社会生活里有所体现,还表现在家庭生活里。
但是弱化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财产权益,一定会造成女性家庭生活中的财产权益的弱化①。
就社会劳动范畴而言,女性就业率一般是低于男性的,同时男性多集中在正规性、高收入、管理性的领域,反观女性只是在临时性、低收入、服务性的岗位上任职。
在家庭里,男性承担的家务明显比女性少,特别是在一些地区及城市里的低阶层家庭体现得尤为显著。

繁杂的家务劳动让不少女性丧失了提升的能力及进修的机会,所以他们在劳动领域中竞争力不强,直接出现经济收入的不均衡,离婚后的生活质量明显降低。
总的来说,女性财产权益被弱化,一定会出现女性经济地位上的弱势。
而只要离婚,男性陷入离婚时的贫困比重,会大大低于女性。
需要注意的是,司法过程中,性别意识发挥的作用也不能完全轻视。
提高性别意识能够使性别观念得到改变,推动司法公正。
但就现实审判而言,法官一般会带着个人的性别倾向开展审判,同时由性别倾向所出现的性别认知更多的潜伏在法官的大脑当中,所以常常发生性别不同的法官对同一性别当事人的态度是有相应差异的,对不同性别当事人的态度同一性别的法官也是有明显差异的。

审判离婚经济帮助案件亦是如此,倘若请求主体是女性一般情况下会获得法官的同情,如果是男性就是相反的。
主要原因是男性一般被当做强者,生活进入困顿期也应该自谋生路而不是向女性求助。
很明显,这是对男性弱者待遇的不公正。
总而言之,经济帮助体系的高度使用被传统的性别观念所阻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