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以来的诉冤制度传统和五代时的变化
导语:唐以来的诉冤制度传统和五代时的变化
制度沿革与立法原因
唐至五代诉冤制度沿革
自垂拱二年设立瓯函以后,唐代的直诉形式即以投瓯为主。与此同时,唐律明确禁止越诉。此后,随着投瓯性质的演变,在文宗年间经历了数次有关瓯使、检验副本等制度的反复后,唐代的投瓯直诉制度也就此基本确定。至五代时,尽管诉冤法律制度的构建尚不如后来两宋时的周全,但此时各朝中央也大多设有接受投状的直诉机关。
后唐天成元年与长兴三年,后唐朝廷先后发布了两道与越诉有关的敕令,其中前者规定只要当事人表示出其“实报深冤,无门上诉&34;者所做的在文书后具以其所诉事由并“监送本处”的规定也并不一定说明此时的立法对越诉行为持鼓励和允许的态度。对观这一时期的后唐法律对已经/未经断遣的诉讼的区分对待可以发现,此时的政策倾向既非全然否定已经存在的断遣的效力,也不鼓励当事人将未经断遣的诉讼提起越诉,而是采取遣送回原地、令当事人逐级陈诉的政策,即从结果性诉讼利益上对越诉(甚至也包括直诉)行采取否定或者至少是不鼓励的态度。
因此很难说后晋继承的一定是后唐明宗初年允许越诉的政策,而不是其晚期的不鼓励越诉的政策。

立法原因
应当承认,唐初设瓯(尤其是其中的申冤瓯)的目的与立法者意欲纾解世间冤抑不无关系,而值得注意的是,五代(特别是后唐初期)之所以显示出较之唐时对越诉的限制放宽的政策趋势,也与朝廷意图表现出为民伸冤的姿态不无关系。
但是,“纾冤’’并不等于为以词讼为主的民间诉讼提供上诉审程序。虽然后世对于唐初设立瓯函的原因的表述并不~致,但无论是将之称为接受告密还是下情上达,其所描述的制度功能实际上是一样的,即为了实现信息由下至上的流通而设。垂拱二年所设的四种瓯函被设计为分别装载不同内容的进状,其所意欲收获的信息也不仅包括百姓冤屈(还包括有关朝廷得失、军国利害的进言),而唐初立法者更曾一度重申接受诉冤诉讼的职能属于三司并因此禁止将此类事项投匦,由此可知,设瓯的最初立意只是为了使阜帝获得各类与执政问题相关的信息。

而综观五代时的立法也可以看出,包括后唐明宗初年敕在内的各道敕文的立法用意也并非为民间诉讼提供上诉审程序,而是为了实现减少狱讼淹滞和冤滥刑狱的效果。先是,天成元年十一月以“近日多有冤滞’’为由取消诉讼程序中的追索其他关联证据步骤,改为一旦获得“赃验’’即行“正断’’,同年十二月并且允许越诉;
此后,928年发布的法律中明显表示出对诸道州府审理结果不信任的态度,并因而要求各地观察防御、团练、军事判官在案成后予以逐一当面录问,“如有异同,即移司别勘&34;为由,取消已被“州府断遣”的诉讼被遣送回当地“依次第论对”的程序步骤而改为“据状施行’’,并只将未经审判、“募越陈状”的越诉案件“具事由……监送本处”。

经过如此频繁的变化之后,后唐法律最终试图实现的是减少狱讼的效果,而不是为上诉者提供司法性的上诉审程序。后晋时亦是如此,朝廷屡屡要求地方官员录检刑狱、以防“淹滞&34;之弊。
狱讼淹滞与词讼投匦
虽然唐代设匦和五代时放宽对诉讼行为的限制性规定的目的都并非为民间提供上诉审程序,但它终究还是导致了普通词讼上诉增多的结果。早在唐大历十四年即有婚田、财产诉讼的当事人越过本司、省司和三司而投瓯进状的记载,而投匦者常常是以词讼冒充军国重事投瓯进状。五代以后,这种现象并未减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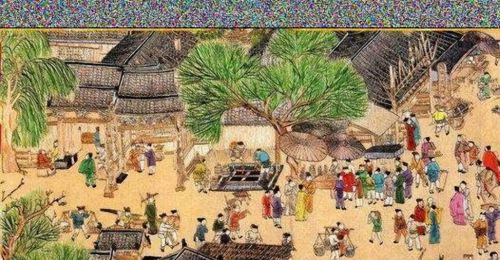
后周广顺二年,朝廷重申百姓诉论应“先诉于县”的原则和显德四年再次申明受理诉讼的务限的法令,不仅说明此时朝廷对诉讼的法律管制渐趋严格,也证明了多讼与随意越诉的现象在此时仍然存在。词讼投瓯现象的增多与词讼上诉需求的增多恐不无关系。
在同时存在严格的经三司上诉制度和相对较为随意的投瓯上诉两条渠道的情况下,当事人更倾向于选择后者上诉是可以想见的结果。而唐代后续的禁止性立法则导致了那些希望通过投瓯获得再次审理的词讼当事人势必要将自己的诉状伪装为军国重事,如此才能实现其目的。
另一方面,从前述后唐立法的演变过程即可想见多讼与随意越诉现象在五代时期的发展原因。由后唐天成元年以后的数年里不断修正诉冤政策的记载可以反推得出:由于朝廷认为基层社会中存在很多冤抑,所以采取了简化审理程序的政策,结果反而导致冤滥的增多,其因此增设逐当面录问的步骤,以求对审理结果进行监督。

然而,当面录问的效果显然一般,否则就不会过了三年后又要嘉奖能雪冤者,也不会发生“皆是讯鞠多时&34;,后又改为直接执行已经被地方机关审判的案件的判决结果,而将未经审判的越诉案件遣送回原处。
事实上,针对地方上狱讼淹滞的频繁指责和反复立法固然说明当时可能存在地方司法黑暗的现象,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朝廷对于地方官员的极端不信任。正是这种不信任导致了其立法政策的多变,这在前述天成三年敕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其实,狱讼淹滞的后果与法律本身的草率性不无关系。以天成元年取消对相关证据的取证而只看有无“赃验&34;,审理过程亦简化为“以三指示吏,吏即腰斩”。
这样的审理过程虽然令“无赖之辈,望风逃匿,路有遗物,人不敢取’’,但也导致“枉滥之家,莫敢上诉。军吏因之为奸,嫁祸胁人&34;,其中鼓院与检院的职能均为受理和转呈,而非言事机构和司法部门。
与此同时,虽然邀车驾往往在法律上被限定为通过其他形式仍不能得偿时方可采取的补救手段,但亦为两宋时期直诉形式之一。这一制度亘两宋时期而未有大变。
另一方面,唐、宋律典均明令禁止越诉,宋初的敕令更是对此屡屡重申,予以严禁。晦列然而两宋之际却开始设立越诉法,此后相关立法逐年增加,其内容包括可以越诉的事由、受理越诉案件的机关、越诉查实后的法律后果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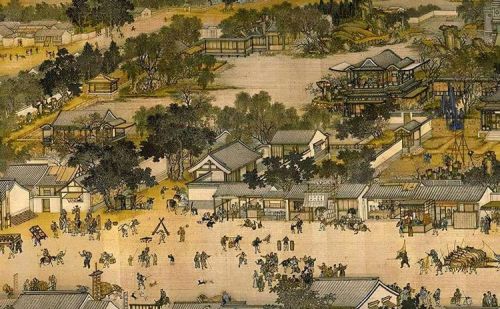
越诉法的设立原因
对于两宋之际越诉合法化的现象,此前的研究一般倾向于认为是出于朝廷宽恤民力或是昭雪冤狱的心愿,虽亦有学者指出越诉法在钳制州县官吏的同时也有钳制地方豪强的意图,但是钳制州县官吏被认为是宽恤民力的辅助,而钳制地方豪强只是在结论处捎带提及,并未详论。
就此时允许越诉的内容来看,确可得出立法者有意于钳制州县官吏的违法害民行为,但如因此以之为惟一的立法原因,则似不能全面涵盖史料中所反映出的问题。观察上表可以发现,两宋各朝设立越诉法的起因并不仅限于钳制州县官吏的违法害民,甚至未必是以此为始和为主:在《宋会要辑稿》刑法部中,最早一次允许越诉的时间是在宋徽宗大观三年,其所针对的并非仅是州县官吏,而是针对全体现任/寄居官员、军兵和官物长期占用寺观的行为。

此后政和二年至宣和六年期间的立法虽多是针对州县官吏的违法勾追、收禁行为,但也有两次是针对地方现任官员“私设机轴,公然织造匹帛”这种侵害中央利益的行为所做。因此,将这一时期的越诉法称作钳制官吏违法或许可以说的通,但是若说其均是针对州县官吏和害民行为则难免有些牵强。
其次,南宋各朝所设立的越诉法起因也不完全相同。高宗朝初期的越诉法多与“军兴&34;、“巨室妄作指占……勒取租钱”等词句说明,地方豪强的豪横行为至少是立法者起意许可越诉的触因之一。
在一些时期,立法者甚至会以“虑冤抑&34;而考虑突破现行法律(务限法)的规定,从而对贫弱方给予倾向性政策。因此,不能说越诉法仅仅是为了钳制州县官吏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