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户籍制度松弛的原因(清朝户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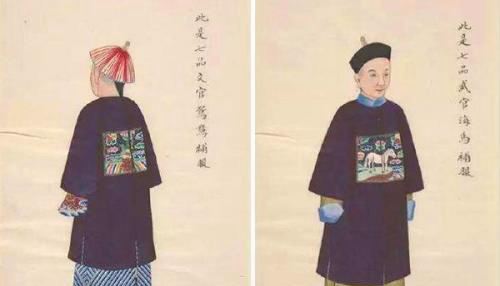
导语:清代为何不以户口钱粮,而以“冲、繁、疲、难”来划定州县等级?
自汉代以后,历代王朝都以户口或田粮评定各州、郡、县的等级。朱元璋建国大明后,沿袭旧制,定粮二十万石以上为上府,以下为中府,十万石以下为下府;县则以十万石以下为上县,六万石以下为中县,三万石以下为下县。
以户口或是田粮来评定地方行政区域的等级,虽说也较为合理,但并不能真实反映一个地方的全部实情。如治理难易程度,民风民俗情况以及地理位置等。到了清代时,最高统治者制定了一个更为细致且公正的等级制度,不再以户口钱粮为准,而是以“冲、繁、疲、难”来确定府、州、县的等级,并形成各种“缺”。下面就来具体讲一讲这种划分方式。
“冲、繁、疲、难”新制的提出清沿明制,入关后也实现同样的州县划分办法。顺治十四年(1657年)后,清政府废除了州县三等制,不过也没有马上实施新的分级制度,“冲繁疲难”的实行其实要等雍正九年(1731年)以后。在这个新制度建立以前,清代各府、州、县员缺也不是完全没有等级区分。
早在顺治十二年(1655年)谕令州、县分三等的同时,顺治帝以直隶的真定、保定、河间,江南的江宁、淮安、扬州、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山东的济南、青州、兖州,山西的太原、平阳,河南的开封、彰德,陕西的西安、延安,江西的南昌、吉安,湖广的武昌、荆州、襄阳,福建的福州、泉州共30府,“或政事殷繁,或地方扼要”,为全国一百多个府缺中的“最要者”,要求京外大臣,“各举才行兼优者,以备三十处知府之用”。
康熙十五年(1676年),江宁巡抚慕天颜,曾以“嘉定政繁多逋赋,陇其操守称绝一尘,才干乃非肆应”为由,奏请行州县更调法,将当时江南省嘉定县知县陆陇其改调“简县”。
由上面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当时的知府员缺已经有所谓的最要与次要之分,而州、县缺中也有繁缺和简缺之别。可以确定的是,雍正朝“冲、繁、疲、难”的办法制定是由当时通行的调繁、调简之法演变而来的。
实际上,促成这个新制演变的原动力并非是雍正皇帝或吏部大员,而是当时的广西布政使金鉷首先提出这项革新用人之法,得到雍正帝的赏识,继而发交吏部讨论。经过一番修订,始告确定。
金鉷在给雍正的奏疏中提到:州县有大小之分,而地方官员也有贤庸之别,在吏部月分铨选,凭签掣缺的既定政策下,往往会有“以庸员而得要地”的结果。因此,为了裨益吏治民生,应尽求“人缺之相宜也”。而要求人缺相宜,各尽其才,则必须做到以下两点,一是以“冲、繁、疲、难”四项定州、县员缺的紧要与否,二是沿用通行的调繁、调简之例。
金鉷的办法确实令人耳目一新。第一,他以一地的交通、政务、赋税、治安情形核定该地缺分的高下,摆脱了历代以户口或田粮定州县品秩的旧有模式;第二,他建议将重要州县员缺化归督抚调补,这使得都督对地方人事有较大的建议权。
此两条建议的提出,对一直苦于人才难求的雍正帝来说好似一大佳音。雍正帝施政最看重人,他曾说:“为政之道,务在得人。”不过,雍正帝认为,用人办事也有轻重缓急之分,州县等亲民之官的重要性更在其他职官之上。他在即位后不久,也就是雍正二年八月十九日即颁布谕旨,指出:“国家分理庶绩,务在得人,道府州县等官尤属要职,其有才干素者,廉洁自持者,不得以时上闻,何以示劝?”
因而雍正帝要求各省地方官,包括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将军、提督,与各道员、知府、同知、通判、知州、知县等官内各保奏一人至三人。雍正三年五月初六日再度下旨,要求“京官自翰林、科道、郎中以上,外官自知府、道员、学政以上,武官自副将以上,旗员自参领以上,皆令每人各举一人”。
雍正六年十月,因“各处需员甚多,而赴吏部铨选之人,不敷拣用”,又放宽保举人的资格,谕令“京官大学士以下,主事以上之汉军、汉人,外官督抚以下,知县以上之满洲、汉军、汉人,每人各举一人”。
由于受保之人中有不少“庸劣幼稚之辈,不当举而举者”,这项各保一人的措施于雍正八年二月奉命停止。
雍正十二年四月初九日,雍正帝颁布谕旨,明白宣布采用金鉷的办法。他说:“朕思各省要缺,交与该督抚题补者,又不至旷延时日,于公事有益”。显然,雍正帝相信,通过督抚题补权的制度化,可以使员缺紧要的地方,获得人地相宜之员。而慎选人才,务得人地相宜之员正是雍正帝施政的最高指导原则。
因此,就雍正帝而言,金鉷的办法正好解决了他心中的难题,他可以好好利用这个新制度,将流弊滋生的调繁、调简法去芜存菁,借以引导地方吏制于正轨。
“冲、繁、疲、难”新制的制定然而,吏部大员显然有不同的看法,他们经过了几乎四年的讨论,一直到雍正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才提出覆奏:
“吏部遵旨议覆。直省道、府、州、县等缺,地方之要简不同,人才之优拙各异,必人地相宜,方于吏治、民生均有裨益。嗣后除道、府员缺系请旨补授,并沿海、沿河、苗疆一切应行题补之缺,仍照旧例遵行外,其同知、通判、知州、知县内,经督抚册报,系冲、繁、疲、难四者俱全,或兼有三项之缺,最为紧要,请令各该督抚于见任属员内,拣选熟谙吏治,品级相当之员,具题调补;所遗之缺,归部铨选。至冲、繁、疲、难四项内,兼有二项,以及专有一项之缺,十居八九。若概归在外题补,恐外省调缺太多,见任属员入敷拣选调补之用,应照例归于月分升迁……”显然,吏部是赞成金鉷的提议的,也就是“许督抚量才奏补”,只是在具体实施的方法上有所更张。吏部在督抚调补的权限上打了一个折扣。金鉷要求凡是“冲、繁、疲、难”四等之地,都由督抚于所属州县官员内拣选调补。而吏部的方案,只有四项俱全或是三项兼全之缺,才由督抚调补,其他兼有二项以及专有一项之缺,仍归吏部月分铨选。
吏部说辞固然有理,但恐怕也只是托词,最根本的症结应该是中央与地方权限分配的问题。如果完全按照金鉷的办法,这就打破了以往吏部对州县地方的人事铨选权。显然,没有任何一个机构会将手上的权力拱手让人。
吏部的这番心思也反映在它的另一项变动措施上。在金鉷提出的建议案中,各省冲、繁、疲、难缺分的制定仅限于知州、知县等缺。但是,吏部可能为了整体的考虑,或是其他未知的因素,将这项办法扩大至道、府员缺。
金鉷所提的督抚之调补权虽然受到吏部的裁抑,但是在他所提方案中的另一个关键问题,也就是各省道、府、州、县之“冲、繁、疲、难”缺分的评定与题报,并未受到影响,仍由各省督抚“注明造册显达”。这当然是由实际情势所造成的,吏部远在中央,无法有效地掌握各地方的吏治民情,不得不仰仗地方督抚。
结论就金鉷的提案与吏部最后定案的情况来看,这场吏部与地方督抚的权力之争,似乎吏部占了上风。然而,从许多督抚题请改缺以及题补的案例来看,却又未必尽然。我们看到许多地方督抚虽然明知会遭到吏部的批驳,但仍然企图经由皇上“特旨”的恩准,或题请将原为请旨或部选的道、府员缺改为题缺。
从各种案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雍正帝、吏部、地方督抚三者在清代政治生态上的微妙关系。“人地相宜”是三者一致认同的目标,但三者对如何达成这个目标却有不同的做法。
吏部是谨守分寸,力求制定完善的制度。地方督抚却希望在制度里多争取一点生存的空间,所以有时未曾考虑本身做法合例与否。而皇帝的做法则因时而异,有时强调吏制的不容破坏,有时却允许督抚的违例题请。
显然,为求达到“人地相宜”的目标,一国之君的考虑施具有多样性的,确保主从关系与掌握绝对权威的重要性可能远远超过对吏制完整的维护。诚如雍正皇帝所言:“用人乃人君之专政,如但循资俸,则权移于下人,君无用人之柄矣。”在传统皇权的统治下,“特旨”这扇窗子是永远必须存在的。
雍正帝将各省府、州、县重新以“冲、繁、疲、难”的标准划分等级,从客观的角度来看,的确是顺应了时代的发展,起到了更好的治理地方的效果。但从主观上来看,这种划分等级的出台,其实也是各方政治利益角逐的一场大戏。
本文内容由小洁整理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