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的佛教政策(隋朝佛教对文化的影响)
导语:历史的尘埃——隋文帝佛教意识形态的全面发展(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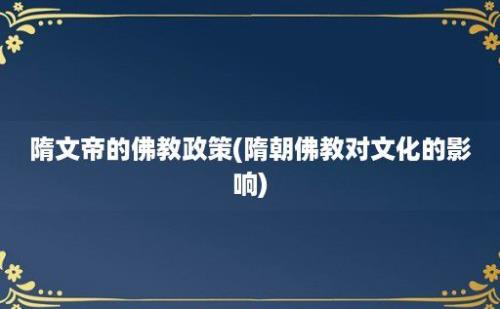
(一)迅速确立佛教教化总部,全面兴建地方弘法中心
阿育王在实施佛教教化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他除了在都城设立有实行佛教教化的总部“阿育王僧伽蓝”外,还在地方造有“如来神庙”,作为地方教化中心。文帝正依此办理。《续高僧传》卷十九《法藏传》载:
大定元年(581)二月十三日,丞相飞龙,即改为开皇之元焉,十五日奉敕追前度者者置大兴善寺为国行道,自此渐开,方流海内。
所谓“前度者”是指此前宣帝下令拣选的“旧沙门中懿德贞洁,学业冲博,名实灼然,声望可嘉者一百二十人”。杨坚大象二年作周相后,这一百二十位僧人由高僧灵藏和竟陵公共同检校,重新剃落,“并赐法服”。现在,这些僧人又奉敕“置大兴善寺”,“为国行道”,意义非同寻常。如果仅仅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宗教理想才复兴佛教而不是为了发展佛教意识形态,文帝就不会说此举是“为国行道”。开皇二年,大兴善寺又移至新都。大兴善寺位居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它的重新扩建、机构设置都与有隋以来为推行佛教意识形态而实施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息息相关,并深刻影响了隋唐佛教的历史和隋唐的政治史、文化史。
除了确立大兴善寺作为推行佛教教化的总部外,杨坚称帝以后,马上在其以前经历的四十五州,统一营造大兴国寺。《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乙载:
(文)帝昔所龙潜所经四十五州,及登极后,皆悉同时为大兴国寺。
《辩证论》卷三也说:“始龙潜之日,所经行处四十五州,皆造大兴国寺。”正如阿育王把其国内所立“八万四千佛舍利塔”均称为“如来神庙”一样,隋文帝对所立寺院都叫做“大兴国寺”。不仅如此,文帝的诞生地冯翊般若寺、文帝之父杨忠曾就职的隋州
也都重建或新建大兴国寺。《辩证论》卷三载:“以般若寺故基造大兴国寺焉……又以太祖往任隋州,亦造大兴国寺。”
统一命名反映出这些寺院同一的地位、同一的作用,即每一个“大兴国寺”都是隋文帝在各地推行佛教意识形态的中心。这种统一命名寺院的模式亦被武则天沿用。除此
之外,开皇元年(581)三月,杨坚又下《五岳各置僧寺诏》:
门下:法无内外,万善同归。教有深浅,殊途同致。朕伏膺道化,念存清静,慕释氏不二之门,贵老生得一之义,总齐区有,思致无为。若能高蹈清虚,勤求出世,咸可奖劝,贻训垂范。山谷闲远,含灵韫异,幽隐所好,仙圣攸居,学道之人,趣向者广。西泉栖息,岩薮去来,形骸所待,有须资给。其五岳之下,宜各置僧寺一所。
山野林泉本为道家栖息之所,五岳更是向来被视为中国名山,文帝在此诏中虽然释、道并举,然而,五岳之下,“各置僧寺一所”突显出文帝借助王权张扬佛教“高蹈清虚”、“勤求出世”的用意。在文帝看来,广建佛寺不仅可以奖劝“学道之人”“贻训垂范”,而且还能够用来“增长福因”,“奉资神灵”。开皇元年七月,又于襄阳、隋郡、江陵、晋阳等杨坚之父生前经行处,“立寺一所,建碑颂德”。其诏曰:
门下:风树弗静,隙影如流,空切欲报之心,徒有终生之慕。伏惟太祖武元皇帝,穷神尽性,感穹昊之灵,膺录合图,开炎德之纪。魏氏将谢,躬事经纶。周室勃兴,同心匡赞,间开二代,造我帝基,犹夏禹之事唐虞,晋宣之辅汉魏……积德累功,福流后嗣……思欲崇树宝刹,经始伽蓝,增长福因,微副幽旨。昔夏因治水,尚且铭山,周曰巡游,有因勒石,帝王纪事,由来尚矣。其襄阳、隋郡、江陵、晋阳并宜立寺一所,建碑颂德,庶使庄严宝坊,比虚空而不坏,导扬茂实,同天地而长久。
“帝王纪事,由来尚矣”,文帝建寺立碑的目的除了遵循古例外,主要还是以此追思太祖武元皇帝“积德累功,福流后嗣”的丰功伟业。因此,诏书利用大量篇幅记述其父杨忠“造我帝基”的历程:
往者梁氏将灭,亲寻构祸。萧察称兵,拥众据有襄阳,将入魏朝,狐疑未决。先帝出师樊邓,饮马汉滨。彼感威怀,连城顿颡。隋郡安陆,未即从风。敌人骋辅车之援,重城固金汤之收。乃复练卒简徒,一举而克。始于是日,遂起汉东。萧绎往在江陵,后梁称制,外通表奏,阴有异图,心迹之间,未尽臣节。王师薄伐,帝之阳是其心腹。于是鸣旅推锋,诛厥放命,继其绝祀。有齐未亡,凶徒孔炽,连山巨防,艰危万重,晋水执钺,假道北邻,皮服钦风,烟随雾集,悬兵万里,直指参墟,左萦右拂,麻积草靡。虽事未既功,而英威大振。齐人因以挫衄,周武赖以成功。尚想王业之勤,远惟风化之始,率夷狄而制东夏,用偏师而取南国,岂从汤征葛伯周伐崇侯而已哉。
从“梁氏将灭”,“先帝出师”,“一举而克”到“后梁称制”,“帝旅推锋”,“继其绝祀”直至“有齐未亡”,“虽事未既功,而英威大振”等等,文帝最终把其父杨忠与商汤、周武相提并论,从而表露出文帝慎终追远的心迹。为此目的,他还要求“每年至国忌日,废
务设斋,造像行道,八关忏悔,奉资神灵”。除了为先帝立寺颂德,文帝还在战场建寺立碑。《历代三宝记》卷十二载:
(开皇元年)八月,又诏曰:门下:昔岁周道衰,群凶鼎沸,邺城之地,实为祸始,或驱逼良,或同恶相济,四海之内过半豺狼,兆庶之广咸忧吞噬。朕出车练卒,荡涤妖丑,诚有倒戈,不无困战。将士奋发,肆其威武,如火燎毛,始无遗烬,于是朕在廊庙任当朝宰,德惭动物,民陷网罗。空切罪己之诚,唯增见辜之泣。然兵者凶器,战实危机,节义之徒,轻生忘死,干戈之下又闻徂落。兴言震悼日久逾深。永念群生蹈病刃之苦。有怀至道,兴度脱之业。物我同观,愚智俱愍。思建福田,神功佑助。庶望死事之臣,菩提增长。悖逆之侣,从暗入明。并究苦空,咸拔生死。鲸鲵之观,化为微妙之台;龙蛇之野,永作颇梨之镜。无边有性,尽入法门,可于相州战地建伽蓝一所,立碑纪事。其营构制度、置僧多少、寺之名目,有司详议以闻。
文帝深刻认识到兴建塔寺在发展佛教意识形态过程中的巨大作用,不但京师确立佛教教化的总部大兴善寺,而且各地还广设弘法中心大兴国寺。塔寺不仅可以作为佛教教化的中心,奖劝世人“高蹈清虚”、“勤求出世”,还可以用来建碑颂德,“庶望死事之臣,菩提增长。悖逆之侣,从暗入明”,充分发挥了塔寺形象的表法作用。
免责声明:本站部份内容由优秀作者和原创用户编辑投稿,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法律责任。若涉嫌侵权/违法的,请反馈,一经查实立刻删除内容。本文内容由快快网络小美创作整理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