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说仁义(孟子的仁义是什么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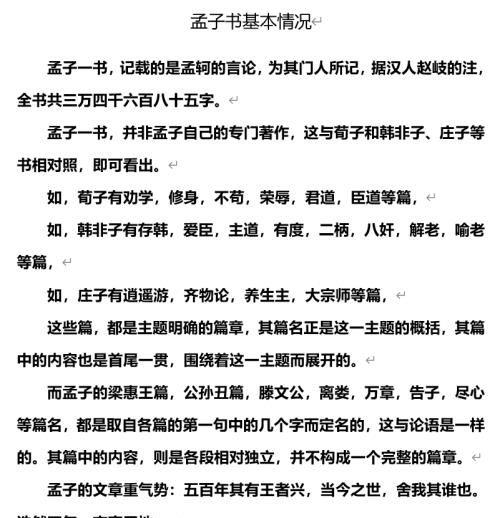
导语:《孟子》所讲的仁义与心性是怎么回事?
早期的儒家经学并不重视《孟子》,唐代韩愈开始赞扬孟子,到宋代程朱把《孟子》列为四书之一,与五经并列,这才使《孟子》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得到很大提高。但程朱所重视的《孟子》是以其中的心性问题为重心的,把《孟子》的思想做了很大阉割,使之成为让人们只重视个人心性修养的学说,而放弃了《孟子》中对君主诸侯的严厉监督与训导,这是对《孟子》的极大歪曲。日本人对《孟子》的思想认识得非常到位,他们不讲《孟子》,认为《孟子》之中对君主诸侯的严厉态度,是对他们的天皇制度的大不敬。宋以后的程朱理学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只让人们学其中的心性之说,而不讲孟子对君主诸侯的严厉态度。
所以我要先把《孟子》中关于仁政的思想完整地讲出来,再来看孟子所说的心性是怎么回事。
简单地说,孟子所讲的心性,是要让人做一个有着充沛的浩然正气的君子,这样的君子是对现实中的君主诸侯保持着严厉监督与批评之责任的。浩然正气,就是为了坚持人类的真理与正道,而不是像程朱那样只让人做一个谦谦君子,而忘记了这种浩然正气与重大责任。
《孟子》所说的心性问题,都与仁义有关,二者是有机的整体。
在《公孙丑》上篇,有孟子与公孙丑讨论不动心的记载,公孙丑问:
不动心有道乎?
孟子说:
有。
他从养勇的方法说起,他认为养勇有三种层次,从北宫黝到孟施舍,再到曾子,层次越来越高,这都是关于心性锻炼的问题,属于心性问题的初级阶段。
再进一步,就要提升到养气的阶段,即以志统率气,所以养气的本质是养志:
持其志,无暴其气。
由此更上升为: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这种气的特点,是“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
但志与气都不是终点,最终则是“配义与道”,即让志与气都从属于义与道,志与气,“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说到底,志与气是义的集合,是义的外在表现。
于是,养心、养气、养志,都以义为根本。所以三者之养,都不能揠苗助长:
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这说明义之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必须在长期的日常生活中,在每件事上都要用心体会义之所在,知义而尽从之,最终才能称为集义,才能把心、气、志养得浩然充满天地之间。
《尽心》上篇中,王子垫问:
何谓尚志?
孟子回答:
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
可知志是以仁义为根据的,则心性的修养与仁义内在统一,密不可分。
心性的问题,本质上是人的问题,即人应有怎样的心性,应成为怎样的人。
孔子论人,以仁为中心词语,即人必须仁,求仁得仁才是真正的人,即君子之人,这是孔子的人格理想。孟子思考人的问题,就深入到人的心性层面了。
孔子论人必须仁,还是比较笼统的说法,到论及人的心性,这个问题就深入了一步,就比较具体而微了,就有了着手处。
孔子论仁的时候,弟子们往往不得要领,不知从何处着手。
到孟子时,他就把这个问题具体落实到人的心性上了。所以说孟子论人的心性,是对孔子论人必须仁的深入发展。但不管怎样说,根本问题是人,是要人达到仁,从最高层次的仁具体化,就到了义的层次,所以孟子论人的心性就紧扣着集义的问题,使人的心性修养与义紧密结合在一起,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事情,都要让人的心性(志、气都从属于心性)与义紧紧结合在一起,不能分开。
这样看来,从孔子的仁,到孟子的义,是一脉相承,而又有深入与变化。但义是仁的深化和具体化,本质上它仍从属于仁。所以孟子把仁义合起来说,不是单言仁,也不是单言义。
心性既是人的问题,故与人相关的问题都与心性的修养有关,不能分成互不相干的事来理解。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孟子》中的许多话语,如《公孙丑》上篇中论“何谓知言”:
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从知言说到生于心、害于政、害于事,这说明知言本身是与心性、仁政等问题都密切相关的。因为知言从本质上说,就是了解人性。人的心性,有自己的心性,有他人的心性,都包括在人的心性这个范畴之内。知言就是了解他人的心性,也属于心性修养的一部分。所以,知言本质上是与心性问题不可分的。
《离娄》上篇中载孟子言:
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了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瞭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廋哉!
这也说明要了解他人的内心之善恶,可以通过观察和听言而知之,而所要知者,是此人的内心之善恶,所以这仍是与人的心性密切相关的问题。
待续
有关资料,采自我为学生上课的讲稿。
本文内容由小姿整理编辑!